放大资金,增加盈利可能
配资是一种为投资者提供杠杆资金的金融服务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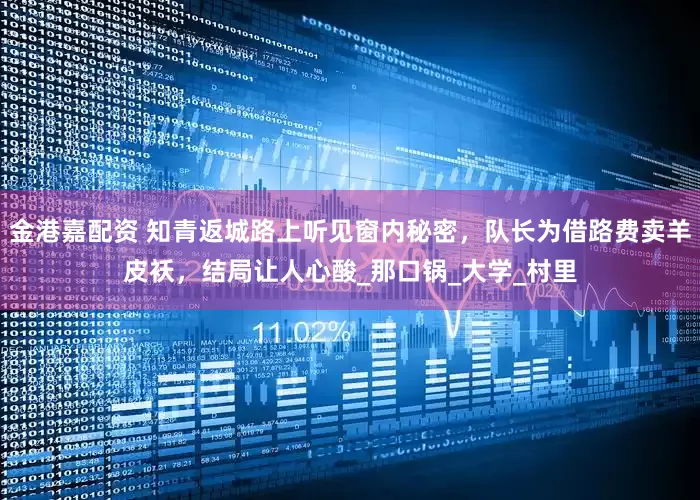
《——【·前言·】——》
1973年秋天,一位年轻知青在准备上大学的前一天,无意间在队长家窗外听见一段话。那不是祝福,不是嘱托,而是一句冷冰冰的现实。一个家境拮据的知青,走出一段全村人眼中光彩的路,背后却藏着一件羊皮袄和一口锅的牺牲。
推荐上大学的知青,从没想过“免费”背后这么贵推荐的消息来得突然。那年,队里把名字报上去时,并没有征求本人意见。谁表现好、谁干得多、谁跟队干部关系稳当,就谁能去。这就是那时候的“推荐上大学”。
刘朝旭是在这样的情况下,得知自己被选中了。他是那批知青里干得最拼的一个,每天农活抢着上,记工分总是高。不是他自愿捐,而是想换个出路。种地养鸡打井干林活,轮了一遍,心里越来越清楚:不想一辈子窝在这片地里,只有拼命干,等有机会能被“看见”。
展开剩余88%机会来了。一纸通知贴在队部门口,说他可以去省里报到,读大学。全村人看他那眼神都变了,有人说这小子有前途,有人酸他“命好赶上时候”。可没人知道他前一晚一夜没睡。不是激动,是愁路费、愁盘缠、愁到了省城怎么办。
家里没有可动的钱,连烧水的锅,都是前不久才托队长买的。当时没说借,只说要个便宜的铁锅。后来才知道,那口锅是队长卖了一件羊皮袄才凑的钱。这事没人当面提过,他也从没敢开口感谢。
带着这份沉重,他走到队长家。本意是打个招呼,说句谢意,也许再厚着脸皮问问路费。他没敢直接敲门,只是在窗外站了会儿。屋里有人说话,是队长的声音,说:“朝旭要走了,给他借点路费吧。”接着,另一个声音冷了些:“你上次卖羊皮袄给知青买锅的钱,现在我上哪儿再借?”
他听清楚了。腿像灌了铅。那一刻,他明白了,“被推荐”不是凭白掉下来的幸运,而是压在别人身上的负担。连锅都是别人牺牲来的,哪还有脸再开口。
走的时候,他一个人去了车站。书包是自己缝的,鞋是自己修的,口袋里只有几块钱,是母亲留给他的全部。他没有告诉任何人,他听见了窗内的话。
车开动的时候,没人送他。他也不需要。他不是带着荣耀走的,他是带着心里的那口锅和那件羊皮袄,走进一个不知归处的未来。
羊皮袄与锅,一个村庄为知青所付出的沉默代价村里不产羊,那件羊皮袄是队长年轻时走亲戚从北方带回的。搁家里十几年,冬天没人舍得穿,生怕磨坏了,留着关键时刻能换点啥。上次要给知青们搞炊事,一口锅卡了整个冬天。卖羊皮袄,成了唯一能筹到钱的办法。
队长自己没吭声,骑上那辆老凤凰,去了二十多里外的集市,把袄卖了。换回来一个铁锅和两袋玉米面。回村那天,天快黑了,他一句话没说,只把东西放在厨房角落。
没人夸他,没人责怪。但全村人都知道,这事是他办的。从那以后,家里再也没有厚点的衣裳,入冬靠烧更多柴火熬过来。
知青来村里,初是新鲜事。干活不顺手,文化倒多了几分,看着就跟村里孩子不一样。有人烦他们,说吃得多干得少。也有人疼他们,觉得这些城里孩子苦命。但村里人再怎么议论,都知道,他们终究是要走的。留下的,是村里人的日子。
锅买回来之后,知青能自己做饭,不用再挤公社食堂。炊烟一冒,有了家的样子。可锅底下,是羊皮袄的代价。队长媳妇记得那笔账,不是记仇,是记下了家里的拮据。一个锅换来的,是一年没添新衣。
谁都没想到,推荐名额落在刘朝旭头上。他是干活最稳的,也是最安静的。不争不抢,一门心思地往前走。他走的时候,没有多余行李,带走的只有希望和沉重。
队长媳妇说的那句“我上哪儿再借”,不是拒绝,而是实话。家里确实没得可借了。她没有骂,没有赶人,只是说出了实情。窗外听到的那个人,心里再清楚不过。他走的时候,没有回头。他知道,这份恩情,不该再加重。
村庄没留住他,也没亏待他。羊皮袄、锅、路费,每一笔都真实得像账本,但从来没人清算。那些年,谁家出点什么,都是默默地扛过去。知青走了,光彩在他身上,但风霜在村里人心头。
走后,他没写信。也没人问起他。在那个通讯匮乏的年代,一个人从村里走出去,就像石头丢进深井。水响一下,便归于沉寂。
但那年冬天特别冷。队长咳了两个月,屋里点了整整三堆柴。烧得多了,锅上的烟也重了。那口锅,成了知青留下最沉的痕迹。
城市的大学生和村口的锅,永远在两头的记忆里从车站踏进城市,他不是踏入新世界,而是走进一个更深的沉默。他不是那种能在人群里迅速找准位置的人,在大学,他就像被人遗漏的那一笔账,总不在别人的交谈和热闹里。他沉默、节俭、小心,不敢松懈,也不敢高兴。
他知道自己的起点,从不幻想轻松翻篇。室友换了几批,朋友没有一个。他常常一个人吃饭,一个人图书馆里坐到关灯,宿舍熄灯后还在床板上默念农学书里那些专业名词。有时背着书包从图书馆回宿舍路上,他会突然想到那口锅,它那时可能还在冒烟,而城市的街灯下,脚步声孤单得像冷风打窗。
家里没寄钱。他不想让家人有负担,更不想让他们知道城里的一顿饭要几毛钱,那时候是一笔难以下咽的数字。他去打零工,给人修表、抄课表,假期去帮人插秧,干什么都行。别人都在忙着恋爱、跳舞、做演讲,他只管活着,干净地活。
直到有一天,他收到一个小纸包,是寄存的行李里夹带的。纸包没署名,里头是一双手工缝的布鞋和十元钱,夹了一张写着“照顾自己”的小纸条。他认出是队长媳妇的字迹。他没哭,但那晚在水房洗完脸后,蹲在墙角坐了很久。
他终于撑过了几年,从大学毕业,到分配工作。他回了趟老家,但没进村,只在镇上买了几样东西,让杂货铺带回村里,说是“感谢过去照顾过的老人”。他不想被认出来,怕人问他混得好不好。他知道自己过得不算差,可他更知道,有些东西已经还不上了。
那些年,他在城市里成家、买房、稳定下来。再也没人提起那口锅,也没人知道那锅底下压着一件羊皮袄。他想起时会笑,但那笑不轻松。他每年给村里寄点年货,不写回信,不打电话,就这样默默维系。他知道,这辈子可能再不会有人提起他走那天窗下的事,可他会一直记得。
第四章:羊皮袄的温度,锅的铁锈,还有他不敢还的情回城后日子慢慢安稳。他从资料员升到科室主任,再升为副所长。城市的生活开始规律,每月工资卡上按时到账,孩子进了重点小学,爱人也调入单位。周围人说他命好,熬出了头。可他心里清楚,这份“熬”不是凭空来的。
每当夜深,他坐在阳台吹风,总想起队里那段路,想起推车去地里干活时路上的尘土,想起队长用旧毛巾擦汗的样子。那块毛巾好像还在家里抽屉里,没舍得扔。他知道,自己的书包、锅、鞋、书费,都不是自家的钱,都是别人的牺牲垫起来的。他知道那些账谁都不催,但他自己不能不还。
某年夏天,他带儿子去旅游,特意绕道桂西小镇,说是看风景。其实他心里有数,那边再过去十几公里,就是那个小村。他没敢进村,只远远在田埂边站了一会儿,教儿子认玉米、稻穗、麦苗。儿子不耐烦,说这些不重要。他笑笑,没解释太多。
那口锅还在村里。后来他托人带过一次电饭锅,说是送乡亲。他没说那是还礼,只说是“家电推广”。那天晚上他失眠很久,躺在床上数着年头,心想:“这电锅能顶不?能顶羊皮袄吗?”没人能答。只能靠自己一笔笔记着,还着,不张扬,不吭声。
有次开会,碰见一个老知青,说起知青岁月满脸自豪。他没插话。别人说他们那村干部贪吃懒做,搞不出成绩,他听着冷冷的,心里翻起一阵刺痛。他想说,不是每个村干部都那样,有些人连衣服都能脱下来给知青,但他说不出口。他知道,说了也没人信。
这些年过去,那批知青老了,有的写回忆录,有的开讲座。他什么也不写,只在单位里踏实做事。直到有一天,收拾旧屋时翻出一本泛黄的笔记本,上头写着:“铁锅已补第二次,锅盖已换。”
那行字下面没署名,但他知道是谁写的。他看着那笔迹,眼圈一下就热了。
这事他没再跟别人讲,锅的事、羊皮袄的事,都藏心里。他知道,城市给了他一份稳定,但村庄给了他一口锅,那锅里装的不只是饭,是恩,是命,是他从不敢轻易提的债。
发布于:山东省尚红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